开挖朱家山河,对于滁河下游两岸人民有诸多好处。诚如吴武壮公长庆向清廷的“秉稿”(报告)所说:
“滁州、全椒、来安等地绅士禀请疏通朱家山河,使滁河之水直接由浦口达江,不必远绕六合。不然每当山水涨发,来不及流入大江,洪水往往已冲决漫淹滁河两岸。若从江浦开浚通道,分泄滁水,直出浦口江面,则永无壅溢之患,而沿滁圩区水灾可消除。此事关系多地方水利。”
但开挖朱家山河之议为什么从明朝起一直议而不行呢?
据吴公总结,共有四个原因:
(1)承办不专也。就是工程承办人不够专心,领导有责任。
(2)民夫势散也。就是施工队伍不够专业,也不够尽力,队伍有问题。
(3)经费太啬也。工程量浩大,经费不足,经费有问题。
(4)求效太速也。工程量大,各级政府官员却一味求速度,欲速则不达,指导方针有问题。
这是前朝的情况。到了本朝,大家都很重视这项水利工程,“康、雍、乾、嘉全盛之秋,高公(高晋)、鄂公、陈公,为此事痛苦在怀,把公事当作私事来办一样在心在意,多次重启这项工程,并亲临监视,然而仍不能完工”。这回又是什么原因呢?“议者辄谓六合阻挠所致,遂彼此相詈为奸”。原来,当时有一种舆论,以为是六合在阻挠工程的开展,不肯配合,导致工程每每流产。
那么,六合阻挠朱家山河工程的理由是什么呢?综合吴武壮公《禀稿》所述,大约有下列几个:
(1)此工程可能斩断金陵六合之“地脉”。
(2)因滁河上游来水减少,可能导致江水倒灌六合。
(3)水势既分,恐宣泄过尽,必遭旱患。
(4)来自安徽合肥方向的生意有可能一半通过朱家山河分散到了浦口,“六合商贾从此减色矣”。
六合在任谢令(谢县长)曾亲自到吴公的衙门里陈说如上,并说这也是六合绅士、耆老们的共同担忧。
吴公在这份呈给沈制军(沈葆桢,晚清名臣,时任两江总督)报告中,逐条加以驳斥,沈制军也非庸庸碌碌之辈,在批复中予以充分肯定。归纳吴沈二公的意思,如下:
(1)“地脉”之说,渺无可寻,纯属荒唐可笑。
(2)江水如能倒灌,则滁河之出江口——六合瓜步先为害,不待浦口新开之河矣。
(3)也不可能导致六合旱灾。滁河屈曲而东,水路只有一道,故来安首当其冲,六合继撄其锐。若论朱家山河分其水势,也只是略略减少而已,此减少正好让滁河来水恰如其分。更何况滁河流域的五个州、县,地势以六合为最下,假使六合有旱患,则其他各处不为“炎炎赤地”?
何况“黑水河”(由碧泉流淌而成又汇合珍珠泉等水后通往长江的天然河道)地势甚高,挑深不易,即使挑得很深,也只须于张家堡、朱家山二处各建一闸,视水之多寡而闸之,则六合旱涝均无须担心矣。
且同为天下苍生,又何必分地域?拿滁州、来安、全椒、江浦四地来与六合一地较,则利害之轻重,还用多说!
(4)至于生意之利的分散,二公只质问一句话:“以浦、六两邑之农民利益与六合一隅之商贾利益比较,又孰重孰轻?”
况且,商贾之利非但不敌农田之利,且其商贾之利说到底自农田而来。岁丰则货销必畅,岁歉则货销必滞。若以为河开则利分,试问苏锡常一带港汊纷歧,路路可通山东、河南等地,生意之衰旺,到底跟什么有关?商贾必能辨之。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应该再无什么纠葛,但朝廷有人出面反对。理由只有一条,就是:数百年来,此河屡开屡塞,可见此工程非人力所能为。
吴公耐心解释如下:
我曾亲往审察,从前之所以旋挖旋淤,大抵因为挖出的泥土就堆在河岸旁,遇雨之后泥土仍回归河内。此工程量确实浩大。“地势渐隆多者,须开五丈许(十五米多),地势渐低少者,亦须三丈许(十米左右),方能接通大江,总计河道约有二千九百余丈。求效不易,期以三年,庶可规模大备耳。”
而此河一开,有两大好处,这些好处确是两岸百姓日夕期盼的:
(1)兵燹(太平天国之乱)之后,安徽江苏残破之惨烈“无过滁、来、全、浦者矣”,加以近年来连年遭受滁河水灾,其惨况还可问吗?今开挖朱家山河以分滁水之势,直接流入长江,仅二十余里路而已,就不必再盘屈二百余里才能从六合一条道流出去。且“张家堡”以东百余里的六合流域,其圩田居多,亦常常被洪水冲决。山水暴涨之时,六合城外浮桥往往因铁索冲断,淹死许多人。因此,朱家山河一通,则滁州等五州县圩区无破圩之患,即使六合亦可稍减洪水之峰,所以六合也是共享其利的。
(2)大江之江浦段,是一条凶险万端的水道。如果朱家山河开通,上下游来船,沿滨江内河航行,即可避开这一段凶险,则“危境而外有坦途矣”。
两江总督沈葆桢早已被沈公的《禀稿》说服,他在“批复”中仅提出两条建议:
(1)滁州、来安、全椒、六合、江浦等五州县,务必坐下来商议,以统一思想;
(2)仔细丈量有关地段,并细细描出地图,并将勘察结果,报上级有关部门研究。
沈葆桢具体提出施工的原则:
(1)承办工程者务必善始善终,谨慎从事;
(2)经费多方筹措,务必保障;
(3)挖出的泥土、石头,不能随便堆放在河道两岸。至于放置何处,再仔细研究解决。
至此,反对的声音才渐渐消失。
来自六合的反对意见,说到底,是因为开河可能损害部分人的商业利益。
比较六合,江浦居于滁河的上游。滁河源起于合肥之肥东县,最后经六合入江,则苏、皖沿滁河一路的生意一向经由六合出口,而后渡江到金陵,或者转往仪征、扬州方向,则六合尽得其利。如果于浦口另开水路入江,则六合之旧有之利起码半分于江浦。此则为六合反对开河的真正原因。
其余如截断“金陵六合地脉”云云,则纯属耸人听闻的借口;六合人说滁河分流于江浦,则导致六合水灾、旱灾,更是无稽之谈。
一条河,开挖与否,两县纠葛不已,可见利益会蒙蔽既得利益者的眼睛,私利更会让眼中只见私利的人丧失良知!
吴公是今安徽庐江县人,对六合商人争利,犹能超然物外,主持公正。吴公调防山东后,接办此事的左公是湖南湘阴人,更不必纠结于地方权势人物的态度,对开挖朱家山河的各方利弊,洞若观火,并凭着朝廷重臣的地位,一锤定音:挖!
不过,左公仍然耐心地对施工的必要性、历史上施工的曲折、施工的诸种措施,一一作出解答,终于在其领导下,给朱家山河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左公,是拿出进军新疆的智慧来处理此项水利事业的:
(1)调动军营善于攻石之勇丁,先从石工入手,以棉花、火药、凿管通山,层层轰揭。
(2)于下游新开一河,自六合马家桥,历晒布场,以至江浦康家圩止,而达于江,让出宣化桥一带庐墓。庐墓之多,也是以前工程难以顺利开展的原因之一。
(3)将富有开河经验的部队调集朱家山,并先后添调各营,合力赶办。
(4)将能打硬战的福建藩司王德榜部队调来,专攻朱家山石脊。
(5)保障施工经费:共用银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余两有奇。经费之不足时候,移用海军建设费用,务使一万多士兵、庞大的专业技术人员、浩浩荡荡的民工、众多管理人员组成的施工队伍的各项开销有切实的保障。
一条十八公里的河,就这样,饱经口舌之争,费尽千辛万苦,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2018年9月改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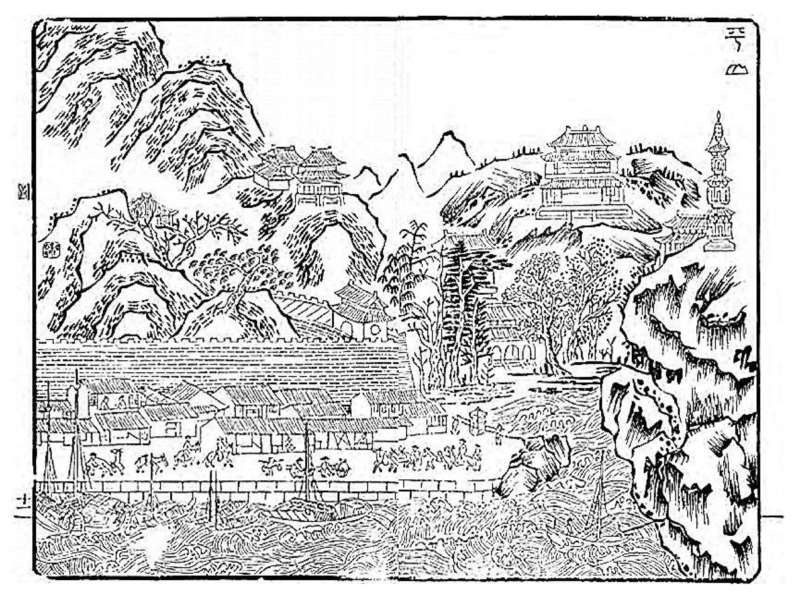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