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的结构性困境
冯绍雷
(本文节选自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
从今天看来,当时苏联的困境是在于出现了一个深刻的两难局面: 一方面中央运用宏观财政干预对摆脱危局毫无成效;而同时现有的结构因素又制约着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尽管当时戈尔巴乔夫还期待通过外交上已作的让步,来争取西方国家的资金援助,然而等不到第二个“马歇尔计划”的到来,一个脆弱的政府结构经不起折腾,终于自行垮将下来。历史,终究是最好的证明,到病入膏育之时再来启动已延宕过久的改革,往往不会推迟,而是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政之所以难容于20世纪末的俄苏社会结构:是由于这一结构先天的制约性。第一,在俄罗斯千百年历史沉淀基础上产生的高度集权并且日益僵化的中央行政管理模式,天生地对于民主政治、法制管理与市场经济具有拒斥性。其次,中间等级的势单力薄使得无论是民主、法治还是市场经济都失却了天然的支持。最后,高压之下所不可避免的体制外的“灰色社会”无处不在,使得旧体制在面临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反而倒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其回旋的空间,苟延其生存,但就长时段而言,对旧体制起到消蚀作用。下面对这三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1
复杂的历史传统
从历史上看,俄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基本上是拜占庭式的帝国统治、蒙古鞑靼所带来的东方式国家管理再加上本土传统所形成的个人专制这几者的混合物。孤立而分散的村社基层单位非但不能与上层行政权力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相反,通过联甲制度等措施加队攮合的对基层控制,使得权力运行的方向始终只能自上而下,而不能由基层上达。
一次又一次的面向欧洲的学马与改制兴有使得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政变。非常奥期君赛是30年代苏共党内党外的大清洗运动。一边是党中央行政权废的号令之下,成千上百万公民被赶进集中营,放逐西伯利亚或者死子命。有不可计数的家属、亲友遭到株连和磨难。但令人惊讶的另一涉却是全国上下热火朝天的斯达汉诺夫建设运动,是史无前例的高速业化进程。罗曼·罗兰1936年访问苏联之时,亲眼所见的苏联人民的来自基层、发自内心的狂热革命情绪正是这一幕场景的一个缩影。
对于俄国多年内外因素所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政治结构,曾有一些机会进行更替与改良,例如1905年革命之后,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推行过宪 政制度;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断断续续也算有过四届杜马;但那些战战兢兢的国会议员们不是诚挚地感谢沙皇所给予的“人民代表”的头衔,就是含着眼泪不时称颂“权力无限”的专制皇帝。
十月革命的发生,是人民对专制的胜利,是进步对愚昧的标志布尔什维克党与千百万民众的卓绝努力并非没有希望改变传统的权大机制,但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使得几十年来争取民主的相当部分努力被转化为以社会主义为名义重构金字塔的进程。
2
中间派的式微
专制主义的威权之下,一个必然的结果便是中间等级和中派主义力量的萧条式微。整整一部苏俄历史上,均不见中间等级发挥决定作用的传统。以稳健平衡、逐渐推进为特色的政治中派主义在俄国很少能博得政治精英与人民大众持续的拥戴。或是保守、或是激进力量之间的相互替代,几乎垄断了俄罗斯的所有政治进程。俄苏历史表明,当政阶层把必要的改革耽搁得越久,日积月累的经济危机就越尖锐、摧毁性的社会爆炸就越强有力,激进派在社会运动中也便越占上风,于是,渐进改良派的处境便越加不利。而中派主义与中派力量的孱弱又反过来延宕了改革的健康行进。这种历史的逻辑在19世纪以后的沙俄时期以及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苏联尤为显著。
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变化实际上现代化的进程已对体制变迁提出了要求,但在沙皇专制的底护之下,有利于市场体制推进与中间力量形成的制度变革始终被延宕。到了 20世纪之初,斯托雷平这一轮改革过于迟到,已无力防止20世纪俄国翻天覆地的革命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未被贯彻到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在革命队伍内部,还是在社会经济部门都缺乏支撑这一变革的稳健力量;在国内外特定背景之下,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终于占了上风。
集权体制多年延续以来,虽有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主要领导人不同程度上希望加以改造,但都因举措不当或得不到支持半途而废。于是,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与被变形的意识形态弄得麻木冷漠的广大民众制约着改革力量的成熟;而另一方面熟悉市场经济的中间等级的缺乏也始终使改革缺乏物质力量的支持。实际上,到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体制病人膏肓,留给以后改革家的余地已经很小了。
从俄国人民的心理特征来看,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绝妙地共处于俄国人的灵魂之中 : 一方面是循规蹈矩、敬奉权力,一方面却又酷爱自由、藐视权威。在多年历史积淀之下,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是俄罗斯民众的信仰所系与希望所在。
革命可以打倒旧日的政治权威,但新的政治权威仍可以在改头换面意识形态保护之下获得新生。村社式的直接民主形式,使基层民众的愿望可以直接得到表达,可以使他们的参与感得到满足。政治权威可以直接诉诸于民众进行政治动员,而民众可以直接求助于权威来进行管理。加之俄国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尚不充分,俄国民众不习惯于复杂而中立的程序化设置,这也使得与市场经济比较接近的专业化阶层始终得不到长足的发展。也许列宁本人对政治折衷主义的痛恨可以被认为是这种民间心态的集中反映:革命不需要那么多的过渡环节,因为革命需要的是敌友之间界线清晰,是非黑白分明。
3
特权阶层与灰色社会
高度中央集权与缺乏中间等级的结构特征,必然导致第三个结构特点,那便是:特权阶层与“灰色社会”的相互依存。
对于苏联特权问题的讨论几乎是耳熟能详,苏俄独具的特权阶层也已经被冠以各种名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诺夫曾认为,苏联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南斯拉夫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认为这是一个“新阶级”,而法国贝特兰教授则进一步命名之是“国家资产阶级”。"英国学者希勒尔·蒂克廷则称之为“独立的官僚政治集团”或者“权贵集团”。他认为,这个“权贵集团”还没有形成为一个阶级,理由是,这个集团的全体成员都觉得他们的地位和特权不牢固,坐在权力象牙塔尖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说不定哪一天也得掉下来。
由于个人的势力和特权完全来自职位等级,因此这个集团必然在两方面进行斗争。作为个人,每个人都不得不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或使自己能升官晋爵而使出浑身解数;作为整体,这个集团必须呕心沥血,使它的下一代也要安享荣华富贵。苏联的权势集团与资本家不同,在取剩余产品方面只有部分的控制权,因此必然要同时实施政治控制并使劳动政治化,以补足它对劳动力拥有的部分控制权。这个集团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决定了苏联社会的性质。另一些学者干脆把这一集团的名称与其职业与专业领域相联系,称其为“军界工业界集团”。
上述评论显然不能简单地视为西方对苏联的攻击,因为,在控制异常严格的70年代初期的苏联社会学著作中实际上也承认:“社会不平等不仅是前一社会制度留下的遗产,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出来的。”
与特权阶层的形成相对应,在苏联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非政府控制的、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并且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灰色社会”。道理很简单,既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利益集团已把公众赋予的政府权力、国家机器视为个人、家庭、小集团宗派谋利的工具,那么,公民便不必对这个已被挟持、阉割的权力所控制的官方社会负责,应该早早地疏离体制而另辟蹊径。对于这样的一个难以名状的社会存在,权且称其为“灰色社会”,是因为它没有西方社会所标榜的那种鲜明政治色彩,而只能栖身于体制之外的色彩模糊之处。
其实“灰色社会”与特权阶层并非两不相干的现象,“灰色社会”作为特权世界的对立物而问世。社会愈不公平,便愈有这样的“灰色社会”出现。但特权阶层又是与“灰色社会”互补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有好处,反正躲在阴暗角落处,天高皇帝远。统计数字已无情地表明,早在80年代中期在全国服务领域,“影子经济”中周转的资金达160亿到180亿卢布,正好超过国有服务领域一倍;而同时,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那一年)国营企业所实现的日用服务仅为90亿卢布。按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戈德曼估计,到90年代中期大约不少于40%的俄罗斯经济处于国家司法权限的监督之外。这些数字表明,非官方社会的经济活动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官方控制的水平。
所以,实际上,俄国的“玛菲亚”(所谓“黑手党”)也并非都是人们所想像的凶神恶煞的破坏与犯罪分子。据笔者的感受,有不少人把凡体制系统所管理不及的领域、组织和人都称为“玛菲亚”。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法制管理十分无力与混乱的情况下,这些“玛菲亚”除了一部分恶性犯罪团伙,有相当部分对于官方社会而言,实际上还是起着调剂余缺作用,特别是在法制管理不及的地方,他们甚至还起着社会稳定的功能。
如果,政治中间力量、政治中派主义的长期医乏,使真正的改款缺乏物质承担者;如果说,集权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共生,使得稳健而深刻的改革缺乏实施空间;那么,特权阶层与“灰色社会”的相互依赖,则通过安抚与姑息,转移着社会的矛盾与掩盖着旧体制的弊病使人们眼开眼闭地听任着整个社会一步步地深陷危机,而又不立即危及个人的地位与生存,不立即危及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稳定。
这不光是迄止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俄国社会的既定政治前提,而且在客观上也使“不打破既定结构,就无法实施改革”的激进心态得以萌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谈史局”(ID:tea-history)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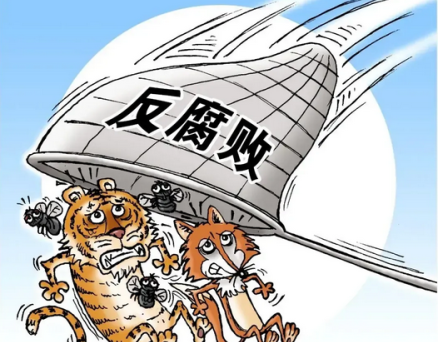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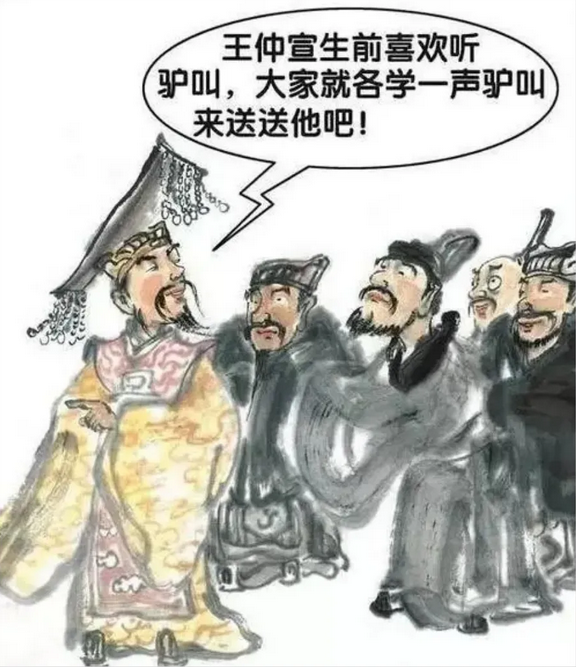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