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柔性引进教授),来源:微信公众号“知本论”(ID:cutalk),本文原载于政治宪法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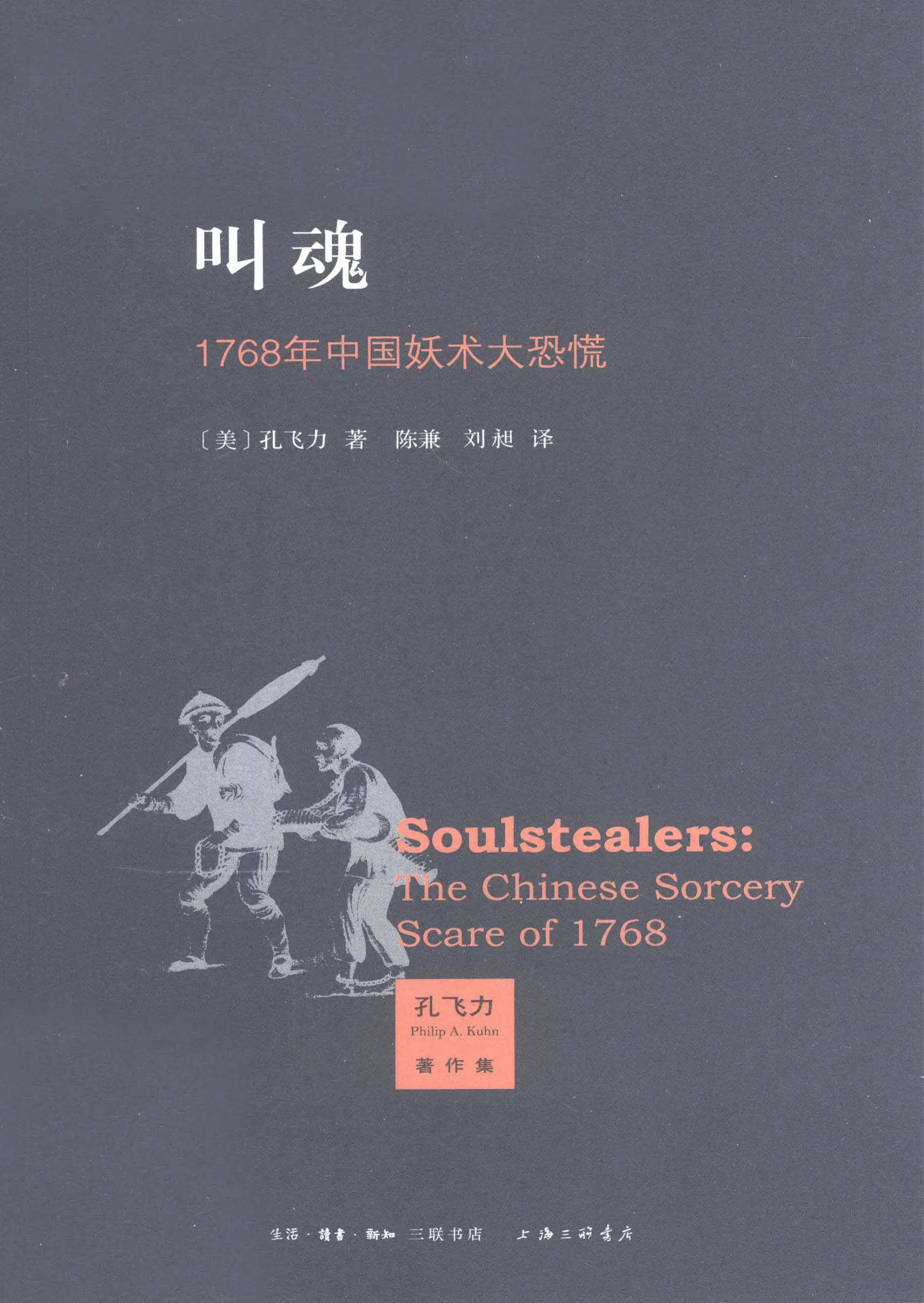
2020年3月,疫情期间,居家看书。
印象最深的是孔飞力教授的力作《叫魂》。孔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叫魂》是他的代表作,这本史诗般的作品读毕罢人拍案叫绝,使我这个几乎从不习惯写读后感(因此也不太会写)的人,忍不住要说几句。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叫魂》是“小题大做”的典范,它以“叫魂”这一事件作为引子,勾勒出18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叫魂”妖术在几个月内搅得半个中国不得安宁,人心惶惶,民间和各级官吏乃至皇上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孔飞力教授据此对当时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阐述,“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其“以小见大”的功力,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孔飞力教授是那种既才华横溢、又肯下笨功夫的学者,“为了做这项研究,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复印了原始档案”,“装了满满的一大纸箱”,可谓“下足了档案研究的功夫”,其治学态度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或许出于专业的习性,我还是最欣赏书中对当时中国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描述和解析,并将其大致概括为臣-民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
一、臣-民关系
“叫魂”作为一种妖术“起”于民间,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的无知、愚昧、轻信。他们身处底层,即便生逢盛世,也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极易偏听偏信,且有一种迅速传播谣言、添油加醋的巨大能量,由此掀起了一场汹涌的社会恐慌浪潮。书中对引发这种底层恐慌的经济原因,如人口过度增长导致的粮食短缺、人均资源比例恶化、银价上涨引起的米价腾跃,民众的社会生活由此受到普遍威胁等等,做了冷静客观的叙述,使得看上去蒙昧荒诞的民众躁动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即便是在乾隆盛世,基层官吏中也充斥着不少地痞恶棍,他们贪婪、蛮横又无能、愚钝,对老百姓凶残恶毒,动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叫魂”案原本是一桩普通官司,但经他们处理后却迅速发酵,演绎成一巨大的社会丑闻,“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几乎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
但案子到省一级时,“官员们因为远离肮脏的县府大堂上的种种压力与诱惑,对于被告的偏见也就小得多。”省里的官员们在判断上是比较明智的,“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也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更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守土职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与秩序,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出于官僚制度照章行事的本能,“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期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事实证明,如果按照省属官僚精英的处理方式,底层民众的恐慌应该能够得以遏制,渐渐平息。然而由于乾隆的介入,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二、君-臣关系
地方官员息事宁人的态度使他们很自然地“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不仅可以给上司一种地方上‘平安无事’的印象,地方官本人也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事件,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同时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
但乾隆通过自己在各省的“眼线”知道了该案,并为之愤怒,他最痛恨的是官员们集体的“瞒报”行为,是那张官官相护、共同对他封锁消息的网络,这是绝对的不忠行为!他的这种震怒无疑使各省官僚充满恐惧,原先官员们“捂盖子”的默契立刻瓦解,山东巡抚“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剿,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并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在官员们的互相攀比的情况下,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
地方官僚精英对“叫魂”的判断一般是不会“拔高”的,“没有人会轻易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但乾隆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他高屋建瓴,习惯于从政治上审视一切,将事件上升到有人企图颠覆朝廷、密谋叛乱的高度,他认定(其实是猜想、没有证据)有一股势力“正在利用剪辫一事来煽动汉人对大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作为皇帝,他最关心的是江山社稷,对谋反之类的苗头始终保持着高度戒备,这种站位的“高度”可能使他高瞻远瞩,但也可能令他神经过敏,从而出现判断上的重大偏差。
君臣关系在“官僚君主制”下原本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官僚们总是希望有一套规范体系,进而照章办事,而君主天然地想摆脱体制的束缚,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如君权与相权的长期摩擦),一些突发事件往往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在“叫魂”案中,这主要表现为君对臣的防范猜忌之心,官僚们的表现让乾隆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汉人官僚们一直以来并从未真正消失过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汉人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得以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于大清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也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官僚士大夫文化的腐败积习“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清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正是由于乾隆对官僚队伍长期存在的这种不满,使得对妖术的处理很快演变为一场官场整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
其实很多官员在内心深处未必认同乾隆无限拔高的“阴谋论”判断,但却不愿、不敢发声,“当事涉敏感的‘政治犯罪’,尤其当皇帝本人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时,惯于‘揣摩上意’的高级官僚们是很少再敢于抗命直言的。因为处于君主任意性权力的威胁之下,事实上并不存在受程序保护的真正安全的沟通渠道。”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君,按说他的判断力不应该太差,但越是英明的君主往往越讨厌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确有不合理之处,但他们总是夸大其弊端,试图彻底砸烂制度的“枷锁”而为所欲为);胸怀大志的君主又往往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自信到自负的地步,死要面子,不肯认错,因此有时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直至把上上下下折腾得筋疲力尽;同时他们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又格外严重,明察秋毫,甚至疑神疑鬼,到处是政治斗争新动向,“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潜藏于各个角落,因而处处设防、戒备;由于他们自身的精明能干,对于下属的“欺上”、“蒙上”等行为也格外敏感和不能容忍,对“服从”、“效忠”的需求分外强烈,这使得他们似乎有一种定期整肃官场的癖好,动辄撤职、降级,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此彰显皇权的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剿越来越成了皇帝与各省官僚之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
如果说叫魂案“起”于民间的话,那么其“终”则在上层少数身居高位的大臣,“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疑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他们的态度从协助皇上进行清剿,转而开始考虑“如何善后”。这一方面需要他们的道德勇气(具有这种胆识的高官在乾隆盛世也是“凤毛麟角”,到清末则基本消失殆尽了),同时也需要乾隆相应地接受建议,适时地下台阶。当然,在“叫停”的过程中仍然要找到一套“说辞”,给足皇帝面子,心甘情愿地为其“擦屁股”,对此臣子们自然是十分敏感、格外用心的,展现出他们为官之道的高明技艺。
三、君-民关系
按说下层的民众、中层的官僚和上层的皇帝,其地位和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某些事件的态度往往有、也应该有很大差异,距离越远这种差距应该也越大。然而奇怪的是,从“叫魂”这一事件来看,其中激烈对立的似乎是君臣关系,而非君民关系,相反君与民在心态上还呈现出某些相似之处,如内心都怀有极大的惶恐和不安全感,尤其是在痛恨官僚阶层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奇异的一致,“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当弘历对这些易受攻击的外来人进行迫害时,村民是不会不对之表示欢迎的;否则的话,在抵御邪术的问题上,他们就只有指望对妖术持不可知态度的官僚们为他们提供微不足道的保护了。”书中揭示了在底层对公平正义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时,许多民众对权力容易产生的一种幻觉,“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这是一个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那些平时不可能获得权力的人“会抓住这些偶尔出现的机会,获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 孔飞力教授对民众积极响应、热烈参与“叫魂”案予以了一定的理解(但显然绝非赞同),认为这种社会道德的堕落有其缘由,“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妖术提供了一次权力幻觉的极好机会。
令笔者印象最深的是,该书告诉我们,原来专制社会的皇权也是非常痛恨官僚制度的,也是特别反对官僚作风的,对其下手整治也是毫不手软的,而不仅仅是老百姓才痛恨,才反对,才希望收拾他们。此时上意和民心可能高度吻合,上给下提供机会,使其获得权力并充分感受其荣耀、刺激和亢奋(还可能实现个人的飞黄腾达),下为上出力卖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他们是可以“心连心”的,是能够同呼吸、共命运的!原来这并非我们这几代人才有的经历,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不过那时的皇帝统治术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赤裸裸地去联手下层以壮大自己力量、从而共同反对政敌的地步,毕竟乾隆最不愿意看到、也最害怕看到的是“暴民峰起”,“旧政权的一个基本的政治特征,便是普通民众对政治抱消极态度。那种睚眦必报的领导人和狂热激动的民众勾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的狂暴结合(这正是现代政治“运动”的表征),还是一件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18世纪的官僚们还没有受到这样的致命夹击。”第一个利用民间能量的似乎是慈禧太后,但她利用义和团对付的是洋人,而不是自己的官僚队伍,且并不怎么成功;几十年后的群众运动要波澜壮阔得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为一门真正的斗争艺术,成为抵制各种腐蚀、保证政权永不变色的重要工具。当上下联手炮轰官僚体制时,虽然他们高喊着同样的口号——为民除害,反对特权,清除腐败,打倒官僚,但都是出于保护自己地位的目的,并不具有为对方谋利益的高尚动机,这一点我们过去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看清楚。
总之,“叫魂”案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中民众的愚昧易变和歇斯底里,皇权的猜忌多疑和反复无常,以及受到二者夹击的官僚阶层——他们比较复杂:下层官员经常横行乡里,胡作非为,省级官员一般能够做出明智判断但迫于压力而放弃初衷去紧跟,少数最高官僚的秉公断案则可能力挽狂澜,……当然,这仅仅是个案,并不意味着这些现象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已经足以令人浮想联翩。
凡此种种,使得《叫魂》一书十分耐读,读罢掩卷看天,唏嘘,感慨!
附:《叫魂》一书结尾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但是我们知道,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我并非建议,在这里存在着对于专制权力的某种“宪政”制衡。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在清代,甚至连一个知县都可以在自己的公堂上为所欲为,而几乎没有被绳之以法的危险。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城市号系信息发布平台,城市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